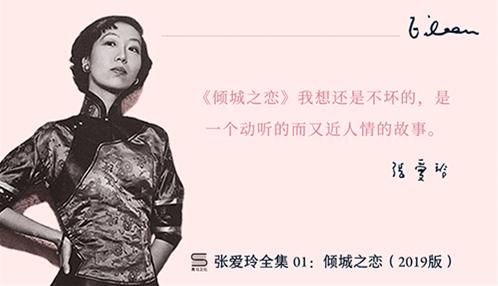电影《第一炉香》开机、电视剧《半生缘》重拍,使得“张爱玲”继续成为今年文艺圈的热词。与此同时,一直在书市常销的张爱玲图书也有了新动态:全新结集的新版“张爱玲小说集(5卷本)”日前由张爱玲作品的内地版权方“新经典”出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五卷本包括《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怨女》《半生缘》《小团圆》。据悉,张爱玲散文、剧本、翻译作品等也将陆续以全新包装的形式推出。
在说到“张爱玲热”时,张爱玲研究者止庵表示:“坦率说我很热爱张爱玲,但我始终不认为她会拥有大众的读者,因为她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作家。她甚至让人觉得,本来生活就挺不容易,读完之后生活更差。但是她就是她,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至于当前市面上版本众多的张爱玲传记,止庵毫不客气地表示:没有一本好的,没有一部值得推荐!
为什么说张爱玲是“传奇”?
止庵与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青年作家笛安一道,做客“张爱玲:传奇未完”的主题沙龙,分享了各自的张爱玲阅读体验。
为什么说张爱玲是一个“传奇”?面对现场现场读者,止庵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有些在文学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的作家,隔了一些年以后只有大学里在讲授他们的作品,或者只是在一些论家的著作里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和普通读者慢慢疏远了,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的现象。
有些人慢慢进入了文学史,但是有的作家一直被大众关注着,有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读他的书,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觉得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耀就在于此,他可能早已离开我们,他可能是我们的前一代、两代乃至几十代、上百代人了,但是他的作品被一代一代的读者阅读和接受,并且能被大家从中读出新意。每个人甚至可以借助作品和早已不存在的作者产生一种交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传奇的内在意思。”
其实不仅是对普通读者,1980年代张爱玲作品重新在内地出现时,也着实惊到了一批青年作家。1985年《收获》杂志第3期首次开辟“文苑纵横”专栏,第一个推出的就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以及柯灵《遥寄张爱玲》。
作家阿城后来写道:“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
止庵告诉在场读者:
“当时有很多作家都对此有非常大的反映,包括阿成、贾平凹等很多人都讲:中国又出现了这么厉害的作家啊。我当时读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跟这个世界之间有障碍和隔阂的,他们需要逾越这些障碍,他们还没有达到目的地,但是张爱玲是直接能到底的。”
笛安的阅读体验,可能更能代表一般读者的心声。
“我十几岁的时候看《倾城之恋》,当时我不觉得是一个爱情小说,我当时觉得这个女的就是想找一个人结婚,她迫切地跟一个人去香港,因为她在娘家待不下去,那个男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小心思。这是我少女时代的一种理解,大人们说的饮食男女可能就是这样的,甚至我到了二十几岁都这么看问题。
后来我三十岁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时候,我又看了一遍《倾城之恋》,此时我才知道《倾城之恋》写的就是爱情。你可以说这两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坚决、不彻底,这两个人性格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绝对是爱情。因为是爱情,范柳原才会在大半夜问白流苏说你的窗子能不能看到月亮。你到三十岁以后再看这一段才知道他想说什么,才知道那个叙述者想说什么。“
张爱玲为何能成为“传奇”?
为什么说张爱玲是传奇,别的作家就不那么传奇?
宋以朗给出了他认为的三个重要理由:
第一,张爱玲的书里有很多金句,可以找得到很多,而且很多人在不停地引用;
第二,张爱玲的人生就是一个传奇,从她的曾外祖父李鸿章到她的祖父、爸爸、妈妈、弟弟,还有她的朋友比如炎婴、夏志清、胡适等等,她的故事丰富得可以写成非常精彩的传记;
第三,与张爱玲的一些照片也有关。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的学生照片还是一个小女生,戴着厚厚的眼镜,不是非常好看。“可是她还没去美国前,去香港的兰心照相馆拍了一套照片,那套照片是我相信让张爱玲成为传奇的一个理由。”
1952-1955年间,张爱玲在香港居住。1954年与宋以朗的母亲结伴去兰心拍了下面这张照片,准备寄给《纽约时报》书评版。
张爱玲自己很喜欢这张照片。据宋以朗编的《张爱玲私语录》一书透露,张说:“我很喜欢圆脸。下世投胎,假如不能太美,我愿意有张圆脸。正如在兰心拍的那张照片,头往上抬,显得脸很圆。”
张爱玲后来多次光顾过兰心。她第二次从兰心回来说:“最好照相拍得像自己,又比自己好看一点。”
从研究者的角度,止庵总结张爱玲的“传奇”所在——
第一,张爱玲与同时期的作家看世界的方法不太一样。张爱玲特别关心的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面对世界,她不考虑这个人属于什么群体、什么阶级。
第二,张爱玲最关注的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有一个立足之地。假如在张爱玲的文学背后有一个张爱玲哲学的话,就是这一点。
“曹七巧为什么拼命地做这么一系列事,从她的同代人到她的下一代?因为如果她不这样做,她的生存就落空了。白流苏也是一样,她之所以要进行一场婚姻的战争,非跟范柳原结婚不可,也是要找到她的立足之地。
我觉得张爱玲始终关心的这个问题恰恰是张爱玲同辈作家、前一辈作家甚至后一辈作家很少关注的问题。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被一代代人读,很大原因是她不断跟下一代的读者有共鸣。在张爱玲生前有很多作家比她有名,比她地位高,但是我们现在读这些人作品的时候共鸣感建立不起来。”
不推荐任何一本张爱玲传记
目前市面上有诸多版本的张爱玲传记,但公认权威者寥寥。宋以朗是在世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张爱玲的人,他的父母与张爱玲相交甚深以至于张爱玲在遗嘱中授权宋琪做自己的文学经纪人和遗嘱执行人,常理而言,他是最适合写张爱玲传记的。
但宋以朗肯定地表示“我绝对不会写张爱玲传”。
“我曾经让止庵老师去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写传记,止庵老师写过传记,所以他写会更好。但是写张爱玲传记目前还是有很多问题,传记应该是一个人的全部,可是张爱玲有些时期的资料太多,有些时期的资料太少甚至完全没有。比如她1947年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那怎么写一个传记呢?目前可以看到的传记都有这种问题。”
作为国内知名的张爱玲研究者,止庵随即说了一句:“我也写不了,这个没法写。”
“第一是材料不够。举个例子,张爱玲跟胡兰成的关系,现在唯一的材料都是胡兰成提供的,所有人都是从胡兰成的书里找材料,然后骂胡兰成。你得有一个旁证,胡兰成说的对不对。
第二个比较难办的是,我以前是有野心想写,但是读完《小团圆》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传记不能写,因为她把原来很多材料都颠覆了。虽然《小团圆》是一部小说,但这里有好多事情都是真的,所以最后等于什么材料也没有。
我认为没有一本好的张爱玲传记,也不向您推荐任何一部张爱玲传记,我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