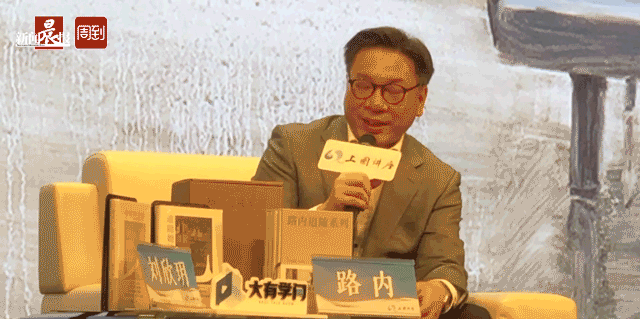2023年12月,临近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路内追随系列”。这是路内以路小路为主人公的四卷作品《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及《十七岁的轻骑兵》的新版集结,也是其首次以完整面貌出版,总体量达70余万字。
近日,路内、毛尖、马伯庸三位嘉宾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与读者分享“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路”。在活动之前,著名作家、小说家路内先生接受了《上海会客厅》节目的专访。
《上海会客厅》节目
对话作家路内:分享创作经历与新年写作计划
Q 新闻晨报·周到:这次在上图东馆的分享活动你给读者带来了哪些新书?
A 路内:这次我带来了自己的几部小说,其中有2022年出版的新书《关于告别的一切》,还有几本作品的新版集结(见“路内追随系列”)。
“路内追随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
Q 新闻晨报·周到:《关于告别的一切》这本书给读者主要讲述的是什么?
A 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是一个讲述。用口语化的说法,就是一个半吊子知识分子从1985年到2019年期间35年的人生,从他的10岁一直讲到他的45岁,他经历过的父子感情、友情、爱情这样一些故事。
路内最新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Q 新闻晨报·周到:在你这些年的创作经历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A 路内:上一本长篇小说《雾行者》(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出版)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因为那本书写得比较久;写了五年,时间过得非常快,五年就像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现在回忆起来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关于告别的一切》也是一种很特殊的写作经验,这个小说我其实没怎么大改,我每写完一段就发给朋友看,中间的话,基本上次序内容调整不大。它对我来讲像一个连载小说,尽管这小说本身并不是连载小说而是整体发表,但它对我来讲是一个连载的写作经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的长篇现在我也不太敢这么写,但唯独这本书是这么写的。
Q 新闻晨报·周到:能否分享一下根据平时的一些阅读习惯?
A 路内:好的阅读习惯是你不要看太多的短视频,不要整天上网,应该多看整本的书,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我的阅读习惯是——我也不太在网上读太多的文章,但是我的书也读得很零碎,可能不足称道,随手拿过一本就开始翻,是这样的一种阅读方式。
“路内追随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
Q 新闻晨报·周到:目前家中大概有多少本藏书?
A 路内:我现在住的房子里大概两三千本书,再多也放不下了。
Q 新闻晨报·周到:关于新年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A 路内:我同时在写两部长篇,如果说其中有一篇写得更顺一点的话,我会沿着那条相对比较顺的路径先走一走。
图1为路内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为读者签名,图2为排队等待签名的读者
Q 新闻晨报·周到:两部长篇能剧透一下吗?
A 路内:(笑)理论上不能剧透。一个是长篇,时间跨度比较大,大概会从民国讲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大概是这么一段六七十年的历史。还有一个长篇小说,大概就是《关于告别的一切》的续篇。这个小说中间有一个断点,就是从2010年到2018年之间我没怎么写,而是直接跳到了2019年,但那个10年其实也很值得写,所以我打算把这个人物中年以后的经历写一下。
嘉宾简介:路内,小说家,1973年生。著有《少年巴比伦》《慈悲》《雾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等。
嘉宾分享:像是回顾青春往事,70后80后有共同记忆
12月17日虽然是上海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当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不过现场气氛火热,几百位读者赶来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分享会。三位嘉宾分别为路小路(路内)、毛小毛(毛尖)与马小马(马伯庸),在台上与读者分享他们对“追随”系列的创作感悟与读后看法,谈论各自对小说人物路小路的认识。
作为对谈环节主持人,在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刘欣悦看来:
路内用了十年的时间创作了今天我们读到的“追随”系列,最早的第一部是《少年巴比伦》,2007年时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算一算路小路来到读者中间已经有16年的时间。路小路打动我们的是他的真诚和浪荡,还有身在迷盲之中依然视死如归的爱和冲撞。所以很多时候开口谈论路小路,我们感觉在谈论自己的青春。
刘欣悦分享个人阅读感言
《少年巴比伦》
华东师范大学毛尖教授10年前在《少年巴比伦》刚一出版之后就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给寄去“追随”系列之后,她又重新读了一遍,作为路内的同时代人,毛尖认为看“追随”系列就像是看自己的青春:
我觉得路内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他们都不是英雄,而且都是有绰号的,和我同年时代的人都很像……所有的人都像我童年时期的朋友,他们也会有绰号。
看“追随”系列就像看自己的青春,说是少年荷尔蒙也好,青春期也好,有一点很强烈,那就是我们身上至今还有那些甩不掉的“少年感”。这种“少年感”在路内的小说中特别明确,包括根据《少年巴比伦》改编的电影(2017年上映),也很好体现了这种“少年感”。
毛尖教授分享个人阅读感言
马伯庸在2007年看到《收获》刊发《少年巴比伦》时,刚刚参加工作:
有一次回老家内蒙古赤峰,我买不到卧铺就买硬座,要找一本能够扛住一晚上的读物,所以挑了一本文学气息比较浓厚的,在北京北站边一个报刊亭卖《收获》杂志,也没有细看,就随便买了一本,硬座一路看完了,看完以后也没有想象的肃穆。
《少年巴比伦》是一个发生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工厂里的事情,这个书里没有太多的苏州评弹,戴着斗笠划船等,路小路遭遇的所有事情我看着都很眼熟。我自己以前在工厂里也有类似的事,也有几乎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并不是地域色彩特别浓厚的小说。
马伯庸分享个人阅读感言
作为1980年出生的作家,马伯庸认为70后和80后这些人是唯一有共同记忆的:
在这之前,大家各在各的地区,彼此不流通,都拥有自己所谓的乡愁之自己的地域特色。到了1990年之后,随着资讯发达,全球化开始,可能每个人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70后和80后那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看到进入中国的东西都一样。
我小时候追《神探亨特》,我的父母看《射雕英雄传》和《上海滩》,包括听的歌曲,看的动画片,“追随三部曲”里打的“街霸”,只有70后、80后这批人有集体的回忆,在前面和后面(的年代)这些回忆都不存在,所以最难抓住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这本书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作者能够写出我们那个年代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