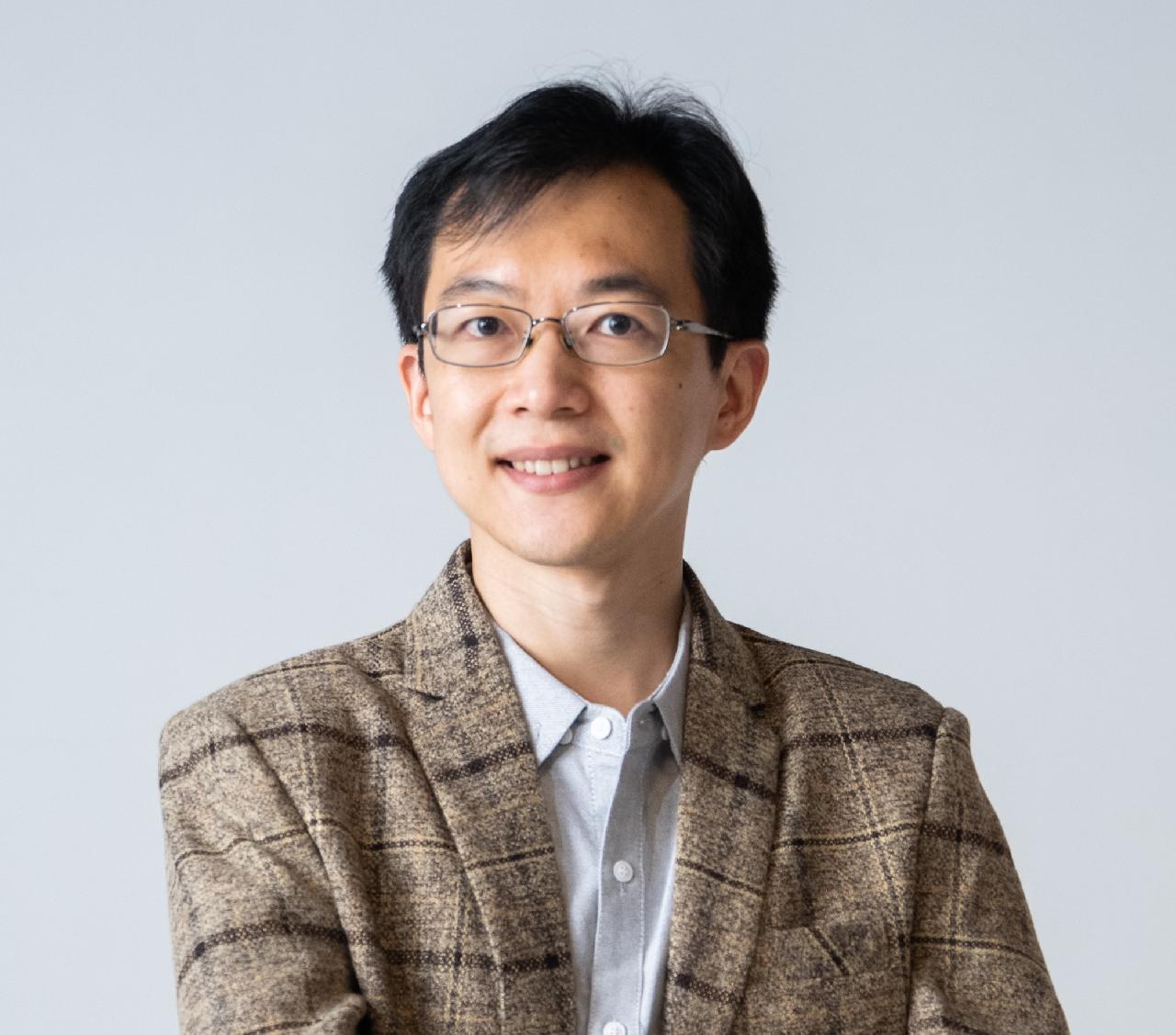如果有人告诉你,能量守恒定律,也许并不是“真理”,宇宙物质可能“无中生有”。你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短视频里,王一字正腔圆地讲述宇宙的故事,打开网友认识的新维度。王一是谁?他讲的是天方夜谭,还是至理箴言?
在剑桥大学,他的办公室曾和霍金毗邻,在香港科技大学,他的大课有百余名院内外学生抢报,在上海天文馆和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里,他编写了相对论的内容……看到这里,爱学习的你,是不是已经重新认真琢磨起他在短视频里的话?
上个月,《新闻晨报》首发同济退休教授、科学姥姥吴於人做主播讲物理引发热议,由此不少人注意到,“职业选手”正纷纷入场短视频科普领域。其实,这些活跃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的学者、教授,都和吴姥姥坚持十六年科普一样,很早就已经涉足于此,比如王一,早在2006年就开设博客讲宇宙,而短视频时代的到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们。
爱物理的少年,成了“宇宙大咖”
出生在辽宁的王一,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初中物理竞赛轻松拿下全省第八名,考入当地数一数二的育明高中后,又拿了物理竞赛全省第十名。
计算机和物理是少年时代的王一最感兴趣的两个科目,但在当时,他并没有多少渠道获取计算机相关知识,于是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进自己喜欢的物理当中,直到后来研究宇宙,也是以研究理论物理的方式开展的。
带着这股热情,他考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系,后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毕业,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论物理和宇宙学。
本科毕业照
宇宙学研究的是什么?
用他的话解读,自己做的就是“宇宙的考古”。
这和我们常提的天体物理学是不一样的。天体物理研究的是具体的宇宙物体,比如某些星球的科学,而宇宙学则是面向整个宇宙,去研究它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这就像宇宙考古,只不过不用学古文,而用物理做工具。”
在剑桥大学工作期间,王一与霍金的办公室相邻。2014年3月,美国科学家宣布发现原初引力波穿越婴儿宇宙留下的印记,这让科学家第一次“看到”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在走廊里遇到霍金时, 王一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对方用拟声器点出了关键参数“r=0.2”,表明他也知悉了这一重大发现。
“霍金教授交流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我们很少去打扰他,尽管他已经很少参与教学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宇宙科学的探索。遗憾的是,我离开剑桥后没几年霍金教授就去世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聊上一会儿。”
2013年至2015年间,王一被授予剑桥大学霍金高级学者,这是一个介于博士后和讲师之间的头衔,此荣誉至今仅有两位华人获得,另一位就是他的科研合作者陈新刚。
王一在剑桥工作时
钻最深奥的科学,讲最浅显的段子
“宇宙对撞机”——这个对普通人来说“不明觉厉”的存在,就是王一的具体研究内容。
陈新刚和他是“宇宙对撞机”的共同开创者,也是在该领域做研究最多的人。王教授解释,这一课题涉及到了组成世界的最基础的物质,以往的工作都是通过一个一个模型去研究,而宇宙对撞机是通过早期宇宙的一般性质去研究粒子物理的性质,不依赖于具体模型。
2006年国际弦论会议。左一蔡一夫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左二薛巍现为佛罗里达大学助理教授;左三王一
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每个字都懂,但连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尽管研究着宇宙起源这一深奥无比的科学,可他的教学,却能用最浅显的段子,带学生理解知识。
离开剑桥大学后,王一来到香港科技大学物理学系任教,2020年晋升为副教授,带本科、研究生课程。其风趣活泼的授课方式,让他的《现代物理》受到学生们的追捧。
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这门原本100人的大课,最多的时候来了120人,开学前他还要专门找到教务处协调换更大的教室,报名的学生一半以上人数都是来自理学院以外,比如工学院和商学院。
曾经有一位其他学院的学生,在提交申请时在选课目的一栏写到——to listen duanzi(来听段子)。这让王一印象深刻。
的确,在他的课上,时常会讲着讲着就蹦出一些网络热梗,或者画面感很强的类比形容。比如解释“光电效应”,他会用打地鼠来比拟,假设地震波来了,地鼠感应到于是纷纷从洞里探出头来,就像高频光波照射推动了电子从金属表面逸出。
他的段子讲法甚至走上了诺贝尔学者大会讲台。
2016年,一张“臣妾做不到啊”的表情包出现在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斯穆特的幻灯片上。在当时,整一个从德国“震惊”到国内学术圈。而这张照片就是乔治从王一这里拷贝走的。
大会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投影片中出现的圆柱体的大金属棒,叫做韦伯棒,是用来探测引力波的。虽然韦伯自己说自己探测到了引力波,但学术圈认为他的实验是不可信的。因此,用韦伯棒来探测引力波,是“臣妾做不到啊”。
2019在加州理工学院参观LIGO引力波干涉仪的原型机
也是通过这张照片,王一认识了在诺奖学者大会现场拍摄到这张幻灯片的苟利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科普大咖。结识同道者,对于他来说,也算是漫漫科普路上的小惊喜。
苟利军的朋友圈(来自网络)
一做科普15年,导师、学生都是达人
王一的课能讲得生动有趣,离不开他十几年来科普研究积累的知识传播经验。在他的身边,不仅有苟利军这样机缘巧合认识的科普大咖,从他的导师到学生,纷纷在做学术的同时致力于大众科普,如同一种传承,从六零后到九零后。
2016年做学术报告时
2005年,正是互联网博客时代兴起之时,恰逢王一刚本从科毕业,受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导师李淼的影响,他也开设了自己科普博客。
李淼老师是很有影响力的科普作家,出版过《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三体>中的物理学》等,他的科普书在同类型书籍中经常销量排名第一。”一定程度上,李淼就是王一开启科普之路的引航人。
与今天声情并茂、言简意赅的短视频科普语言相比,王一坦言十六七年前的科普文章还很稚嫩,“像讲公式的教科书”,一板一眼的文字,更像自说自话而非面向普罗大众。直到几年后参与编辑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才真正理解科普语言的表达方式。
随着近年短视频时代的到来,王一教授在网上刷到了自己学生周思益的热搜,这位九零后的小女孩在抖音上做了科普账号“弦论世界”。
“虽然我在科研和教学里是老师,做科普,我得从学生做起。比如,我可以从我的学生那里学习。周思益是我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工作后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她不仅博士毕业,科研上早已独立,在网络科普方面,她也独辟蹊径,影响力越来越大。”
王一的学生周思益
在这位开门大弟子的介绍下,今年11月30日,王一在自己的抖音账号“研究宇宙”上发布了第一条视频,获得1.9万点赞。他运用此前录制慕课的器材、环境、技术,在业余时间自己搞定全部流程。至今在抖音、快手平台拥有二十余万粉丝。
别看王教授操着一级甲等的普通话水平侃侃而谈宇宙,但生活里,他个性内向,一旦大家的话题从他的专业脱离,他就成了人群中最安静的聆听者。
科普,就是他尽情表达的舞台。从最初的博客,到此后的微博,再到微信公众平台,直至今天的短视频,王一的科普紧跟媒介的发展变化,也伴随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的成长。
与娱乐视频“抢注意力”,粉丝群收获感动
短视频平台后台数据显示,科普类的视频在与娱乐类的视频“抢注意力”的竞赛中,尚处于下风,许多人往往看到科普视频一两秒钟就划走了。
为了跳出“秒划走”的怪圈,让受众第一眼就感兴趣,他对自己的科普方式,比如语言、画面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王一教授常常自嘲,自己是以“街头卖艺”的形式去向大家科普宇宙知识的。因为科普就像街头卖艺,就要去人多的地方,在自己家楼顶上卖艺,那是没用的。去人多的地方,这也是他在网络上科普宇宙知识的初衷。
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如今在网络上将‘艺’卖出去成了我最大的难题。”
因此,在“卖艺”的过程中,他经常跟“有梗的”网友们相互学习,使“阳春白雪”不再“曲高和寡”。
“我用杆子去怼人,这样的过程会不会超光速”的科普视频,当时他觉得在视频中讲解得并不是很透彻,后来在评论区看到一则留言,发觉高手果然在民间:“假设杆子的一层分子推动另一层分子,每推一次都需要时间,以此类推,那么这个过程就不会是超光速的。”这位网友只用了一句话,就将原理解释得简单又明晰。
在王一教授的短视频粉丝群里,任何有关于物理的问题都可以发问。经常有中学生通过网络和他深入讨论,一些私信中也常能见到“硬核”科普爱好者的提问,比如“什么是对称性自发破缺”“什么是汤川势能”,他们不缺基本的科普知识,王教授都会用更加专业的语言与其进行交流。
偶尔,他也会被“问倒”过,比如某个不在自己研究领域的科学知识,他诚恳地告诉学生们,自己不会:“科普视频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而做科研的真实状态则是,不会就是不会。”
这些执着于探索宇宙奥秘的青少年粉丝,也做出过让他感叹自己“何德何能”的事情。
由于粉丝们发来的问题较多,王一教授有时就通过语音来给大家解答,一位有心的学生,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专门开设新账号,通过录屏的方式来分享他在粉丝群中讨论物理问题的语音视频,甚至有个学生把这些语音整理成文字,记录、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
这一条条来自互联网真诚的反馈,让王一教授深受感动,他所付诸的努力没有落空。
科普形式很多种,但归宿终会相逢
多年来,王一教授的科普尝试了许许多多形式,比如撰写书籍、开办讲座、写博客、做视频,还包括天文馆解说词的编写。7月17日,世界最大规模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正式开放,在相对论这部分就能找到他写的文字。
用他自己的话讲,天文馆给到既有“命题作文”也有“看图说话”。许多内容都进行了一字一句的反复打磨才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比如关于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解释,从初版到终版,他反复推敲,推翻修改了三次才定稿;对于这部分的图片解析,他选取了“奇点”“普朗克时间”“爆胀期”“夸克时代”等共7个关键概念,分别用一两句话言简意赅说清楚。
解说词部分文稿节选
这不是王一教授第一次为权威载体编写科普文字,在2011年至2013年,通过漫画科普博士李剑龙的推荐,他受邀负责编写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物理分卷的相对论板块,以及量子力学的部分内容。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可能吗?如果你来到黑洞周围,是有可能的……”
书中,他用这样一个个的小问题勾起孩子们的好奇心。王一还清晰地记得童年时阅读旧版《十万个为什么》时,“钟变慢”给自己带来的认识上的冲击,十余年后他再次与这套书相遇,毫不犹豫接受了编写邀请,并尝试与曾经小小的自己对话,找到最能被孩子接受的语言。此外,他还写了科普专著《一说万物》。
事实上,今年的12月15日,是《十万个为什么》出版60周年之际。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抖音将推出视频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通过打造权威、专业的科普知识平台,让青少年从科学中获得启蒙答案,培养好奇心。汪品先院士、褚君浩院士、杨雄里院士、科学姥姥吴於人、王一……都将利用各自的所长,共同参与其中,他们将《十万个为什么》中的问答以实验、动画、实景装置等各种形式展示讲解出来。
在港科大工作期间,王一在香港天文馆、高中、大学做公众报告,每当有关于黑洞的大新闻时,总能看到他为青少年做科普的报告的身影。
2015年王一做公众报告现场
做科普,是我贡献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个亘古常论的话题,面对无边宇宙如此宏大的课题,王一越来越觉得,个人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社会大众对科学的关注,才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
不论是王一还是他的伙伴、师生,不论是文字、讲座还是视频,科普的形式千变万化,但归宿终会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