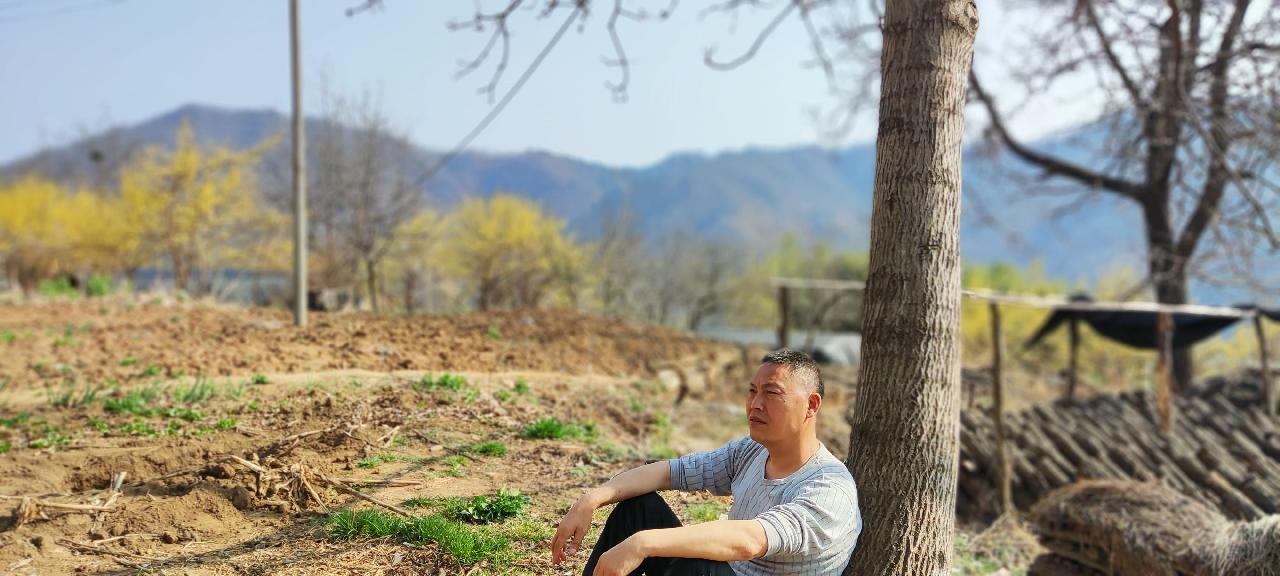在他的朋友圈里,置顶的是一条去冬“吆喝”第一茬冬菇的动态。
这条动态里,“矿工诗人”陈年喜有些抱歉似地解释了涨价的决定。“2018年到现在,一直是香菇45元/斤,花菇65元/斤包邮。今年菇价十分坚挺,湖北河南上门的商贩都出到40多了。”他几乎央求般地写道,“香菇就涨5元吧,因为邮费也涨了……”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年这一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010万人。四舍五入来说,陈年喜也算这里面的一个。
2020年确诊尘肺病后,在外漂泊二十载的陈年喜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陕西省丹凤县峦庄镇峡河村。他的主业仍然是写作,同时也做起了“半吊子”电商,在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里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家乡的特产。
老家交通不便,无法直接收发快递。为了节约快递费用,他很多时候会开着自己那辆摩托车跑上二三个小时去县里发。在村、镇、县之间的穿梭往来,让他对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观察和体会……
今年3月,以27个短篇如同27组镜头那样呈现峡河在历史长河中的岁月与人烟的散文集《峡河西流去》出版。目前,豆瓣上的评分为8.8分。
近年来,读者圈流传一种说法:“当代散文男看陈年喜,女看李娟。”从某种意义上说,近期因为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而爆火的《我的阿勒泰》,和《峡河西流去》在本质上有相似性。他们写的都是自己的故乡,但那个故乡存在于过去的某个时空,和当下已经没有多少关系。陈年喜认为,这是一个故乡消散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失去自己的故乡。
日前,正在北京宣传新书的陈年喜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者专访,谈到了故乡和返乡。他觉得,对于漂泊在外的人而言,返乡永远是一种退路,但更是一种出路。
从“向外走”,到“向里走”
离家和回家其实是一件事
从2019年至今,陈年喜先后出版了5本以矿工生涯为素材的作品。其中包括为他引来外媒关注的诗集《炸裂志》和《陈年喜的诗》,以及散文集《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和《一地霜白》。
如果说之前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向外走”,记录自己在漂泊岁月里经历的人和事;那么,《峡河西流去》则彻底换了方向,转而“向内探寻”。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因为我面临着一个创作素材枯竭的问题。”陈年喜解释,“所以我必须在作品中有一个转向,我要重新去开辟一个新的源地,重新找题材。就像很多作家一样,我想到了去探寻自己熟悉的家乡以及童年少年时期的自己与这片土地的关系。”
陈年喜为新书签售
在这本书的自序里,他写道:
“人一辈子都在做两件事情,离家和回家,做得费神劳力甚至九死一生。其实也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因为离家也是回家,不过是方向和方式不同而已。”
只有经历过离家打工的人才能懂得这句话字面背后的意思,“他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回来,他走出去是因为家乡没有资源,家乡没有这样的条件给他提供舞台。”
“但是在外面唱罢,最后还得回到幕后,那就是家乡。当我们面临着无力前进,对生活感到无奈、对命运前途无从把握的时候,那就要回头看,向回走。”
家乡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漂泊者的退路,但同时更为他们提供出路。这种出路可以是现实中的,也可以仅仅是精神上的。对于陈年喜这样以文为生的人而言,现实和精神的出路双双指向同一件事:写作。
50岁这年的返乡,带着一种无奈。当时陈年喜在贵州,为某旅游企业写文案。确诊尘肺病后,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外打拼。于是他向公司辞职,作为一个无业者——文学创作当时并非正式意义上的全职工作——回到了家乡。
一度,家乡和他彼此陌生
此时,他发现自己和家乡之间已经彼此陌生。“长者衰朽,我父辈那一代人都不在了,而我这一代人因为打工经济全国到处漂流,也很难见到他们,见到也都变得很陌生。孩子这一代更加遥远,和我们几乎没有没话可说。”
有一度,他觉得自己关于峡河的写作困难重重,简直无从下手。后来,他从峡河和它的枯荣兴亡找到了突破口。“峡河七十里,七十里的地理与风烟,包含了多少秘密,我似乎熟悉,又一无所知,”他写道,
“就像我们自己对于自己,更多的时候,也像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
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乡村世界
更多是乌托邦层面的家乡
2021年,陈年喜向《纽约时报》记者描述自己因写作成名后的状态:“你知道自己无法将旧生活抛诸脑后,也无法融入和参与新生活,你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这种尴尬也将伴随他此后的乡居生活。
“现在很多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乡村世界,包括李娟的阿勒泰,它们其实更多的是乌托邦层面上的家乡,但是家乡的现实有时可能很残酷。它不能安放你的灵魂,甚至也不能安放你的身体。”
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寻找更好的未来,乡村开始了凋零的过程。渐渐的,学校因为学生数量的锐减无法再办教育;乡里的小诊所因为一天没有一个病人而难以为继……这不仅是中国乡村面临的现状,也是全世界很多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都不可回避的现实。
峡河人口也在不断减少,回乡后的陈年喜发现,自己曾经每日上学和回家必走的那条小路如今已完全被荒草掩盖。“从童年走到少年,从青年走到中年,哪怕我们一生走到天边,谁也不能从一条路走到另一条路上。”他感慨,故乡是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路已被荒草掩盖
峡河水兀自流淌,他的人生往前走,村庄也在发生着改变。
在峡河,因为没有大巴和公交,出行需要自己开摩托车。不会骑车的老人,就只能靠走。每次回家,最让陈年喜头疼的就是乡道至家的这段路。“摩托车只能开一挡,路长且阻,如果雨雪天,只好两脚泥泞。”
今年年初,村里排除万难对它进行了修整。村支书是他的发小,“是乡村里难得的知识型村官。”陈年喜说,“基层经费之难,难如上青天,他带领的班子还是力克众难做了不少实在的事。”
一个月后,修路工程还在继续,他又用一种温柔又戏谑的语气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评论,
“新修的毛路,像初立锅灶的新生活一样需要填填补补。”
建设家园中,最年轻的留守者也有50岁了
如同神州大地上分布着的无数大大小小的乡村,近10年来,他的家乡也进入了势不可挡的城镇化进程。对于更新中的家乡,陈年喜鲜在作品中涉及,《峡河西流去》这本书总体还是在打捞他记忆中的家乡。他承认,这是因为自己对家乡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难以把握,“有些东西需要时间给它一些定论。”
但他一直在关注乡村巨变中个体的命运。
“如今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他们身体和灵魂的挣扎其实和一、二十年前的情况是不同的。原来我们更多的需要面对温饱的问题,而现在更多是选择的问题,比如说教育,比如将来的人生出路。经济文化始终在向城市走,我们必须跟着走,这样一个主动的但又带着被动的选择问题,其实有很深层的东西在里面。”
当大部分乡村青年如陈年喜所说,仍然在向外走、向城市走的时候,小部分的人却在悄然回归。近年来,一些返乡青年在田间地头或者白墙黑瓦的家中架起三脚架摆放手机,考究一点的配上一块打光板,就开始向网络另一边的世界直播。在直播中,他们推介自己家乡的大好风光,也推介家乡的特产。
而尽管是个人的、疏离的,陈年喜也在不经意中加入了那支庞大的返乡电商大军。
在电商经济时代
乡村世界多多少少有些机遇
陈年喜在自己的个人平台上细致地教购买家乡野生天麻的客人如何保存和食用。
1.放冰箱保存,以免发霉生虫。
2.药用食用时用水稍清洗一下即可,无污染无硫熏,自然采挖自然风干很干净。
3.完全自然环境下生长,个头品相稍逊人工种植的,但品质放心,药用价值很好。
4.如果煮水饮用,可放一块糖,让口感好一些。
仍然是文字工作者那种不卑不亢的口吻,不带一点网络卖家的话术。
因为写作积攒了一定的人气,他曾经考虑过像很多有点知名度的人那样在抖音上带货。但带货是一件自成体系的事,涉及到多个环节,因此需要一个团队。他单枪匹马,没搞成,有些气恼自己。但也幸亏没有收获大面积的成功,所以现在的电商生意只是他的副业。而相对于中国的电商事业,显然是文学事业更需要他来作贡献。
家乡的一些特产,从大山深处走向了全国各地的客户家里
归根结底,这个时代只是过往和未来无数时代中的一个,它自然无法摆脱每个时代自带的、有着明显时代印记的荒谬性,但如今的时代有它的优势,它让陈年喜这样的人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公平,一种在早些年的打工经济时代中绝无可能实现的公平。
他先是在网络上通过写作引发了广泛关注,不但作品热卖——其中《炸裂志》加印16次,而出版于2021年的《微尘》也已经印了12版,并且受到美国多所大学的盛邀,前往交流、演讲。
许知远也曾带着自己的节目组去拜访陈年喜
然后,虽然做得半心半意,他却也实实在在从电商经济中获取了微薄的利益。“我们如今坐在家里就可以把资源卖出去变现,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公平的地方,或者叫机遇,乡村世界现在多多少少有些机遇。”
但当他享受了网络带来的交易便利后,现实世界的困难摆在了眼前。“发快递很难,从我们老家还要走20多里路才能到镇上发快递。”而且他发现,“镇上快递点的收费比较高,随随便便一个小单要15块钱。我卖一单可能只能挣个10块8块的,这样一来等于钱都让快递挣了,自己一点也挣不到。”
攒上多个快递一起发,他自己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
他后来就去县城发快递,要稍微便宜一点,8到10块钱就给发。但县城更远了,从他家骑摩托要走上70公里山路,差不多两三个小时才能到。“现在油价这么高,8块多钱一升,所以一个来回烧油也得40块钱左右。你在县城还得吃饭,还得喝水,所以成本也不低。”
因此他通常累积到10个以上或者20个单,才会去一趟县城。好在会在他这里下单的顾客大都是他粉丝,所以大家即使等待也几无怨言。
其实不止发快递这一件事,陈年喜注意到,“人少的地方,所有的成本都会高。”在他的家乡,镇上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县城,“你想他拉一车菜,要跑那么远的路,烧那么多油,到镇上还可能好长时间销不掉,所以所有的价格都会升高。”
2022年12月,年关将至,他在朋友圈里感叹:
“三月不知肉味,今天去镇上,才知道猪肉涨到了24块,生姜8块,豆腐3.5块。老人说得对,无事莫上街,上街要丢财。”
希望更多人关注我的家乡
让它在消失的路上走得慢一些
因为喜欢陈年喜的文字,很多粉丝继而关注到了他的家乡。一年之中,他要接待好几拨人来参观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有上海的读者提出,想租用他的老宅写作。
“风景之地,多是生存维艰,我老家连公路也不通,上山下坡都要出一身水。文字和镜像本质是骗人的勾当,网络在手,我们都一样,不是在骗人就是在骗人的路上。”
他谢绝了。
很多读者被他的家乡风光吸引
在陈年喜最近的一次直播中,有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留言说,他们已经对他描写自己家乡的作品进行了备案,作为下一部电影创作的备选方案可能会去峡河实地取景拍摄。他对此将信将疑,但又觉得果真能成的话也是好事一桩。
“我的家乡是一个注定会消失的世界,其实我还真是希望有人去关注到它。”陈年喜说,“但我也不希望它像阿勒泰那样,成为一个网红的地方。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这样一个世界,让它在消失的路上走得慢一些。”
和陈年喜一样,村民们享受到国家政策,近年来在县城或者省城都已经有了房子。他们选择在峡河落叶归根,但他们的儿女眼下看来是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们入土为安之后,这个地方就会变为人员的空白地带。但如果还有一些机会,年轻人就可能会回来,它也会有一些延续。”
如果还有一些机会,年轻人就可能会回到这片乡村
网络时代为陈年喜所说的“机会”提供了一种可能,“比如有资方觉得这里可以开展乡村游,或者做一些以读书为主题的活动,通过网络的传播,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光、团建。这样,离乡的年轻人们也许就会觉得家乡还是有机会,就会想到回家发展发展。”
他承认相比阿勒泰,峡河地区要开展旅游观光最大的局限在于本身的景观和物产资源都不够丰富。但因为没有游客,所以一切都还保持着原生态。而在中国众多所谓的古镇和古村落里,真正的原生态已经很少见了。他也曾经自豪地“宣布”,老家的落日比泰山落日更美。
老家的落日
我们在他那首《夕阳记》里感受到了这种美,一种兼具哀愁与慰藉之美:
“多美的夕阳啊 落在
向西的山岗 也落满峡河
多少事物在此时告别
一张白纸看见
诗歌将诗歌还给诗歌
两辆摩托车从山上下来
这是贫穷之所唯一奢侈的事物
两个少年一前一后
他们并不赶赴什么
他们比一阵风更夸张
没有谁知道 是什么
让他们管不住右手
峡河的一天就要这样消失了
经过夕阳安慰的夜晚才叫夜晚
夕阳比生活更加具体
它照耀着平静的村口
走过村口的河水 失意 过去与现在
以及它们杳无音信的结局”
无论峡河将来会不会被旅游热和直播经济带火,陈年喜知道,自己都不会再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