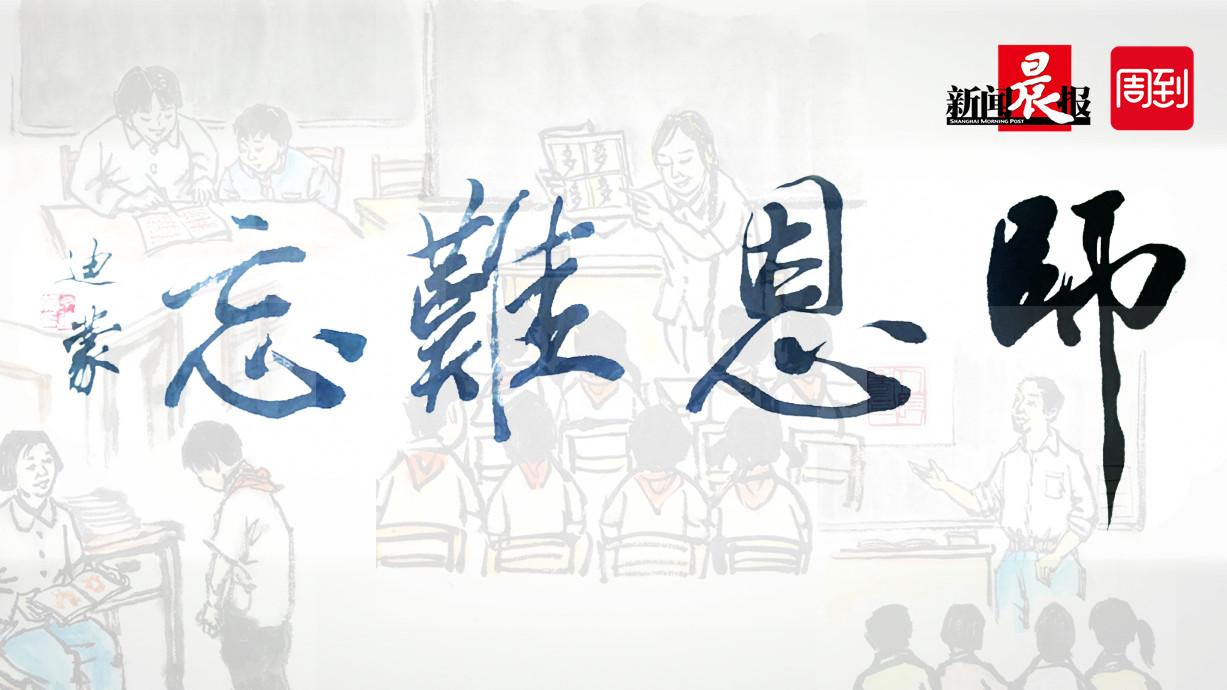今年的9月10日是第40个教师节。一个人的成长初期少不了老师的正确引导,特别是在求学阶段,如果遇到一位好老师无疑会对人生起到重要作用,甚至会改变人生命运。
有道是师恩难忘,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在教师节,我们邀请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市民代表回忆对自己人生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老师。
教师节快乐(词曲演唱:王渊超)
我人生的引路人
罗志华 50后,上海某中学退休教师、漫画家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曾经遇到不少好老师。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小学班主任张彩娟老师。记得我小时候十分好动,大概读二年级时,我又爱上了刻花样(剪纸)。刻好的花样就夹在课本里,上课时就会翻出来显摆一番。当然,这一切都逃不过张老师的眼睛;课后,张老师让我去办公室,但没有没收我的花样,而是肯定了我在美术方面的特长,同时指出文化学习的重要性,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我上课再也不开小差了,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一学期结束之后,我被学校推荐去考上外附小。
对于一个行为出现偏差的学生,张老师没有简单批评了事,而是采用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指出学生的问题,发现学生的长处,进行正确引导,让人改正错误。可以说,张老师是我人生的引路人。多年之后,我也成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而在我的教学工作当中,每每遇到犯错误的学生,我就会想起当年张老师对我的引导。
无意中写了个“多”字
丁迪蒙 50后,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沪语专家
王绮华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刚进小学时的班主任。当时她刚刚从师范院校毕业,我们班是她的第一批学生。她上课极具亲和力,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她。
当年的课堂细节已模糊,但于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字。父母对字要求严,刚上学就规定我每天写毛笔字。记得那次作业有个“多”,我无意中写“多”,自己看看也好。于是就想看看老师会打几分?上课了,王老师拿本子放在讲台上,随即举起一本说:“大家看看丁迪蒙的‘多’,她是怎么写的?”于是,她拿了我的本子,逐排往后走让同学看我的字。被老师认可、表扬,心里是多么愉悦啊!可能,这就是我后来一直坚持练字的动力吧!
多年后,彼此失去了联系。后来,同学又慢慢聚在一起了。每次相聚都要谈论王老师。我更是想念她。于是托学生在公安系统里找查找,颇费周折后,在失散五十多年后找到了。
张可如老师是我在向明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原向明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她有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课上得极好。这位原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上了我后两年的语文课,授课时旁征博引,潇洒自如。后来,我考上了中文系才恍然大悟——当时是大学老师在给我们上课啊!
中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崇明的农场工作。是她,得知有个小学教师的名额,急忙跑到我家来鼓励我去做教师。当时我很犹豫,因我自小胆怯,从不敢举手发言。她说:“练练就可以,老师相信你行的。”果然,我当了五年小学教师,学生也非常喜欢我,说我课上得好。是她的授课风格在我的身上潜移默化;她的普通话也影响了我,在农场里我翻烂字典,成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没有她的两年教学,我高考语文拿不到高分,没有她逼我去做小学老师,我也考不上大学。 感恩老师,不忘师恩!
那堂不照本宣科的语文课
何振华 60后,上海作家、杂文家、资深评论人
王铿老师是我读高中时的副班主任,他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王老师上课绝对不照本宣科,每一堂语文课,45分钟必定有20分钟是脱离了课本内容,他给我们讲唐诗宋词,讲他酷爱的篆刻艺术,讲中国书画,讲中西方历史,也讲述他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而王老师原本就是一位大律师,我高三毕业之前,他就回到华政继续教授国际法,后来担任市政协委员。王老师的母亲廖克玉是晚晴重臣、湖广总督瑞澂的夫人。毕业后有一天他让我去他家,见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周谷城先生写给他母亲的墨迹,“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王老师确实蛮喜欢我,我的作文常常被他当堂点评褒扬,而且破例就让我不在作文课上完成作文。虽然他只教了我们一学期的语文,但我感觉其实已经提前一年进入了大学课堂。
有意思的是,有一趟有人去教导处举报,说王老师的语文课不正规、不谨严、扯闲篇,不利于毕业班的学生应对高考。我和其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步出校园、踏上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是体悟到,当年王老师在课堂上那多少个不照本宣科的20分钟,恰恰是给与我无以替代的滋养。望之俨然,接之也温,这是风度翩翩、儒雅的王老师也不只是留给我这一个学生的深刻印象。
杨老师的绘画创作课
姜浩峰 70后,资深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
我的第一笔稿费,是杨云平老师给的。杨云平老师是我在复旦中学的美术老师。上世纪90年代初,杨老师在搞教学科研探索,他希望中学生用大师眼光看世界、画世界。也就是从自己的心底思索选题进行绘画创作。如果技法达不到,再想办法提高。
我记得在一个学期开学之际,他要求班级同学自己选择,愿意按照传统美术课本学习的坐在一起,想先搞创作的坐在另一边。绝大多数同学愿意先搞创作,我记得自己和要好同学王华一起,还有隔壁班的李平等人经常到美术室去画画。那时候下午三点十分放学,我们会主动搞到五点才离校。日积月累,诞生了几幅水粉材料绘制的作品。又过了一阵,杨云平老师著作《少年画创作教与学》诞生。我也获赠新书。然后,还收到几十元稿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几十元对一个孩子来说不少啦!可见,杨老师大概率将稿费都撒给了学生。我们感觉杨老师真是神了。
回首少年时期那些伙伴,似乎真正从事美术创作工作的一个没有。但我翻翻朋友圈,发现绝大多数同学对艺术、审美等等各种拿捏。杨老师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代代学子,让大家无论是否富贵,都有一颗审美之心,令个体生命更美好。从这一点上来说,绝少说教的杨云平老师,功莫大焉。
杨云平老师在学校开展新型美术教育观和育人模式研究(拍摄于2005年)
后来,杨老师自费环游世界,并创“环球游画”概念。每每看到杨老师新作,一种欣喜之情,油然而生。祝杨云平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教师节快乐,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原来我的作文可以写得很好
胡宝谈,70后,沪语作家,著有长篇沪语小说《弄堂》
小辰光,我是老皮(沪语:非常顽皮)的学生,到处闯祸。老师们看见我非常头痛。张月英老师是我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班主任,也担任语文老师。有一天中午放学,我刚刚从校门走出来,打算回家吃饭去,一个同学追上来叫住我,一只幸灾乐祸的面孔。“张老师寻侬!”我一听,头皮一麻,肯定没好事体。我做好吃批评的思想准备,脚拖着走回去。张老师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面晒太阳,一面批作业。看见我来了,估计也看见我很紧张,她笑了,告诉我用不着这么急跑回来,下午来也可以。她从一叠簿子里抽出一本,是我的作文簿子,翻开来,我看见很多句子底下都用红笔画了圈圈。
张老师告诉我写得很好,还笑眯眯讲了很多鼓励我的话。这是我印象里,头一趟得到老师的表扬。在此之前,我也没觉得自己作文怎么好。之后,我心里有了一个意识“原来我的作文可以写得很好”。我开始有意识地朝这一点前进。很多时候开始做一桩事体,只不过是欢喜。欢喜,可能就来自于一句鼓励,一句“你做得很好”。
小学毕业之后没两年,我就搬家了。虽然没再见过张老师,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一直有“联系”。我写作路上的老师,除了那些文学经典里的大师,也有我小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张老师!